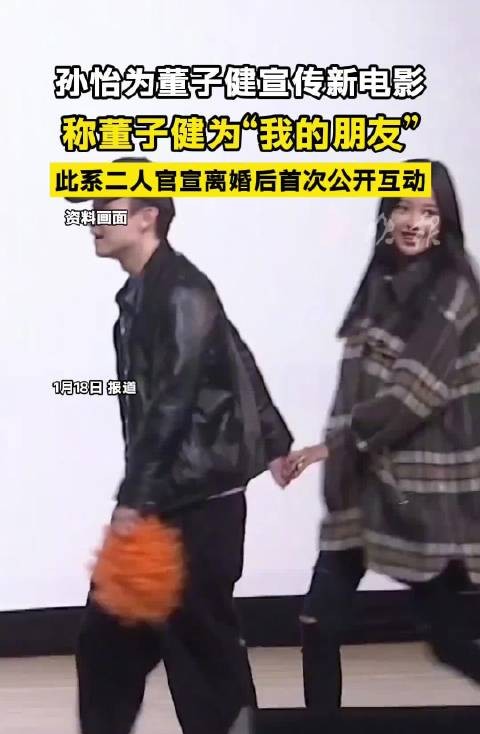以文学沟通世界,他们这样让“局外人”被看见
通过世界遗产,我们可以学习到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生活知识# #旅行生活# #世界遗产#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赵茜
吸引了数十亿人的目光的成功者,为何依然自道“边缘”?
撕开生活的酸甜苦辣,我们如何打响共鸣的响指?
5月27日,浙江工商大学第二届文学周在杭开幕。当天,文学X影视跨界对谈第二场在浙江工商大学国际会议中心报告厅举办,班宇、畀愚、周晓枫、吴越、李晓博五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结合自身创作、生活经历,以精彩纷呈的对谈呈现聚光灯之外的人生喜乐,带来有关自我、他人和时代的深刻反思。

【1】“边缘”的AB面
“每一个辉煌背后可能是无数的心酸,赛场上有掌声簇拥的金牌得主,就有终其一生没获得任何关注的人。”周晓枫曾是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她对“边缘”有独特的理解,“历史上很多商人处于‘边缘’,现在很多小说家也处于‘边缘’,我们对这个词语的解释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要谨慎地判断一个人是是否‘边缘’,不能以外在的标准把别人划归到某种格子,否则就会带来自身的狭隘。”
她认为,面对曾身处盲区里的人,不能仅给予对方表面上的关怀,而要深入对方内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创作是更深层次的关注。”
作家班宇是一名摇滚乐迷,他认为“边缘”某种程度上代表一种抗争,一种在自我坐标里实现理想和价值的愿望:“最近我在听本能实业乐队《滇东幻想症》,里面有一句歌词‘告诉我,时代的精神是什么?跟随巨浪,她骄傲地讲;告诉我,时代的精神是什么?远离巨浪,她悄悄地讲。’从‘骄傲’到‘悄悄’,我想歌词中的‘她’是不是就指代某种自我选择的‘边缘人’。今天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仿佛都处在信息茧房中,与其他人发生的联系越来越少,这也是一种自我选择的‘边缘’,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在这种‘边缘’中,我们或许能认清自己的来路,重新确立自我目标,确定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
在《叛逆者》原著作者、作家畀愚看来,人在世界上是非常复杂的存在,在不同场合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不能依照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边缘”,从这个角度来说,“边缘人”就是圈子之外的人。
“身处不同的场合,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成为目光的反光板,成为不被注视、不被探究、不会引起他人好奇的人,但这其实是一种常态。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那些被刻板印象拼凑起来的人,他们活在别人的定义中,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人去了解真正的他们。”《收获》杂志资深编辑吴越说。
她认为,人只有将自己确认为中心,才有可能在社会的布朗运动中游到某一中心,或者成为某一范围内的主角。而今天探讨“边缘人”的意义,就是破除一些虚妄的仰望,通过这类叙事调整、校正、反证每个人对他人的认知,把原子化的认知逐渐恢复成有血有肉的颗粒。

【2】做自己的主角
“大学期间,我应该是学校里非常优秀的学生,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一个去澳大利亚交换的机会,在异国他乡,因为语言壁垒和文化隔阂,我一度感到非常的落差和挫败,为了缓解这种情绪,我就窝在卧室里看《甄嬛传》。”青年作家李晓博率先分享了她所经历的“边缘时刻”,这个故事引发了几位在场嘉宾的共鸣。
周晓枫聊起她近年来的人生感悟:“我当然希望每个人都很快乐、达观,但如果逆境不可避免,只能将它当作有意义的经历去沉淀。一直处于巅峰上的人可能会自以为是,忽略他人甚至不自觉地去评判、指摘他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所谓‘边缘时刻’有时对你所谓坚固的中心是一种瓦解、腐蚀和撼动,而逆境里长出来的自信也会成为个体价值观的支撑,让一个人的成长变得结实。”
“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自我定义为‘边缘’呢?因为相对于模糊不清的中心,‘边缘人’之间最能取得共鸣。”班宇讲起了他的两篇小说,《逍遥游》和《漫长的季节》,“《逍遥游》中有一个20多岁的女性,她患病之后,她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能抵达的地方变得越来越近,所以她会无比珍惜逍遥的旅程,那些平平无奇的一草一木、毫不出奇的景观,也因此在她心中幻化成多姿多彩的形象。《漫长的季节》小说中的女孩有一位患病的母亲,她必须用大部分时间照顾一位渐渐丧失行动能力的人,并因此丧失了自己的生活,能掌控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这两篇小说写得都是渐渐丧失自己生活能力的群体,他们或许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边缘人’,而我想表达的,就是如何运用越来越少的时间,达到一种充分感受世界的能量和能力。”
畀愚说起了他人生“边缘”的部分:“我出生在一个小镇,30年前没觉得自己和文学会有什么关系。后来企业倒闭,我也不喜欢干其他事,就跑去写作,从一个‘边缘’走向另一个‘边缘’。”这引发了吴越的共鸣,从记者转行文学期刊编辑的她,时常会遇到不知如何解释工作价值的时刻:“我们每天会看大量的文字,其中大多数是没有达到发表标准的。读者之所以能够阅读文学经典,很多时候是因为文学编辑把那些值得阅读的作品挑选出来,送到他们面前。”
她希望读者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就像一艘船找到自己的河流,成为河流上一个自由轻快的生命。

【3】冲破隔阂的力量
写作者怎样把他的记忆和感受转换为文本?
周晓枫说,要放下心中的成见。“对某个人斩钉截铁的定义已经包含了某种傲慢,这意味着我们既不了解自己能力,也不尊重他人生活。我举个例子,北京有个乡村叫辛庄,里面有个小学,一些学生家长在里面开起了咖啡店,在我想象中,这些家长是因为孩子远离城市,最终牺牲了自己的未来,但事实并非如此,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家庭集体作出的选择,它不是传统的奉献叙事,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不管任何写作者,不管你写了多少,都不能带着奖杯奔跑,用自己的概念去套用别人的生活,当你不这样对别人的时候,你的言行、状态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班宇说,写作不是权力分配,无论是对读者还是作者,最重要的都是具备想象力和强大的共情心,“我们今天可以写一个古代的国王或者一个暴君,但也必须承担一个命题,就是被他人书写。书写的过程不是相互反对、相互攻击,而是提供每个人理解这个世界的不同路径。”
畀愚说,一个作家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至于作家说得是什么,读者如何理解,已经不重要了。”读者可以通过作品来了解苦难,也可以试图理解苦难背后温情与人性,这种多元价值的传递,就是文学存在的意义。
吴越说起她一段非虚构写作的经历,“2018年我在新西兰箭镇,这里曾是华人矿工的居住地。华人来这里之后,无法去正式的矿,只能去淘气矿和尾矿,而且住在非常矮小的房屋中。这件事当时给我很大触动,但我并不知道如何去写。“后来,她看到矿工的历史影像,看到矿工告老回乡在广东开平造出的西洋雕花楼,看到一些矿工回乡后无法适应当地生活,再度远渡重洋,直到死亡后遗骨被华侨组织运回,看到华工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捐出启动资金,才打开了情感开关,有了开启一个故事的冲动。
“我们身边有无数精彩的故事,但要把它从一个故事、一篇新闻、一个你熟悉的人衍生为一篇优秀的小说,必须经历非常庞大的思考量。你要把你了解的线索,你本身的偏见一点点编织起来、公布于众,一个严肃的写作才可以发生。”她说。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网址:以文学沟通世界,他们这样让“局外人”被看见 https://www.alqsh.com/news/view/188203
相关内容
以文学重新连接世界——《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新书“首航”他们以生命守护星火,我们才能看见光明!
当商业化进入文学,谁还能像鲁迅一样守住真实世界,他们两个可以
加缪《局外人》:生命的意义不在目的,而在过程丨景凯旋读经典⑩
故事沟通世界,徐则臣对话30国汉学家
看见李雪健这样的作品也是相当的让人具有感染力…
颜南星以纱巾遮眼体会脸盲,江心白看见这幕,内心被触动
文化这一年·文学|文学“破圈”以昂扬生命力感召大众
让世界听到平凡中国人的精彩故事
东西问|刘俊:研究世界华文文学,要看白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