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去》:是小镇女孩的成长史,也是两代女性隔着时间的对望与拥抱
生活故事精选:从小镇女孩到都市时尚博主的成长记 #生活乐趣# #生活分享# #生活故事精选# #时尚生活资讯#
奔向大城市,还是回到小地方?这或许是每个人都曾有过,或将经历的抉择。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出现的大量流动人口,还是新世纪以来,涌向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京漂”“沪漂”“深漂”,亦或是近年来在地文化、在地经济的挖掘与繁荣,“大城市”和“小地方”的抉择,始终横亘在我们面前。
青年作家水笑莹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到上海去》就是在这一主题之下的创作。水笑莹通过小说集里的八个故事,呈现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女性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徘徊与选择。作品内部自有节奏与步调:有人向外奔走,有人困在原地,也有人在两地之间游移、犹豫。大学毕业生、小镇老师、住家保姆、私人家教……作品中的人物境况各不相同,但她们都有着“到上海去”,获得独立的渴望。
“到上海去”并不是某一篇作品的标题,“上海”也并非特指,它可以被替换成任何一个城市,因为“到何处去”,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课题,也是这个时代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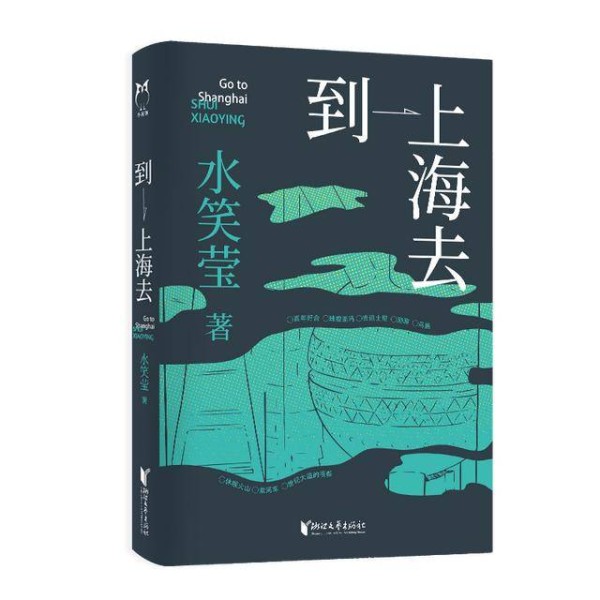
●我们悬浮着,在这座城市
读完《到上海去》中的八篇故事,也许你会发现,主人公们似乎都处在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里。《紫河车》的结尾,成宵丽抛下的一句“明天我不在家,我要去上海。”究竟是对家庭桎梏掷地有声的反抗,还是认清现实后一句无奈的牢骚,尚未有定论。《洄游》中,钟紫冉在老家与上海之间飘忽不定,父亲去世,母亲再嫁,自己在事业上未站稳根基,她甚至不知道,老家拆迁之后,父亲的遗像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同样的,《鸟居》里的芮雪,虽然已经萌生了离开上海的想法,却也并不真的想回到小县城,过上考公考编的生活:“她觉得有一个看不见的旋涡在拼命将她往回拉,她不怨恨任何人,她只是本能地想要挣扎一下。”
小人物那种“本能的挣扎”看似微弱,于生活的大江大河而言,掀不起任何波澜,实则已是他们拼尽全力之后,能维持的最后一点体面。水笑莹将此命名为“悬浮”:面对生活的暗流和旋涡,个体仍然能够保持头部以上浮出水面,等待风浪变小,即使水面以下,双腿已经用尽全力在划动。“如果一个人既无法往前进一步,又缺乏退路,也没有躺平到底的勇气,用尽全力却只能维持眼下的生活,他就会在这种‘悬浮’之中感受到疲惫。”
水笑莹无意在小说里给出解决方案。她的笔尖无限贴近,白描式地呈现这种悬浮其中的状态。比起虚构小说,她更像是修剪去生活的枝丫,沥干了想象,去书写一种近乎残酷的真实。在《百年好合》中,她用近乎冷峻的笔调描写陈俊青为田玲准备食物的场景:“面条有点坨了,她加了点自来水进去,用微波炉热五分钟后,再用筷子把面条和豆腐夹碎成糊状,晾凉。”
书中对“沉默”的书写同样令人震撼。在《百年好合》的病房场景中,“田玲仰头看着输液袋,药水一滴滴往下流。她问田亮几点了。田亮说,快十二点了。田玲说,你不去送外卖吗?田亮说,今天不送,休息,来陪陪你。”这段对话中,人物的沉默比言语更具穿透力——田玲的提问与田亮的回答之间,是病痛与生计的双重压迫;而陈俊青在茶水间的观察,则暗含对护工群体生存状态的批判:“阿凤的饭盒里有鸡腿和百叶结红烧肉,食堂的标价都是十块钱。一顿饭就是二十来块。这么吃哪存得住钱!”这种“留白”式的叙事,让读者在空白处自行填补想象,从而深化对社会现实的认知。
我们心有不甘,我们无可奈何。正像在漫长的“沪漂”岁月里坚持着写作的水笑莹一样,小说里的人物,以及“悬浮”在城市里许许多多的我们,也是抓着一点难得的期待与温暖,努力书写着我们自己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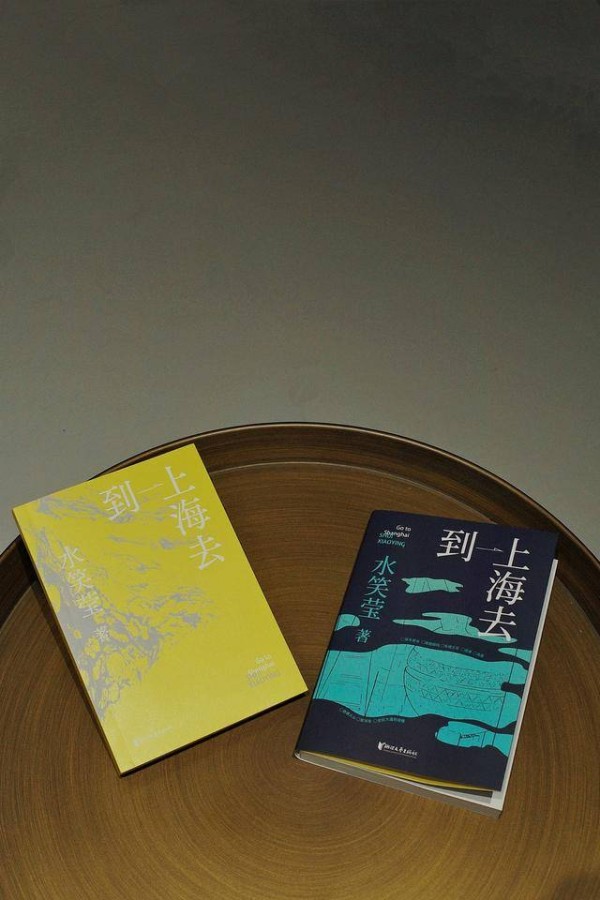
●妈妈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
水笑莹的创作素材,大多来自自己和身边人的生命经验。《到上海去》里,有着明显的一组对照,即“60后”和“90后”的女性,换句话说,也可以看作是母亲与女儿的对照。
谈到创作这些作品的缘起,老家安徽芜湖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水笑莹说,从小她就听说过许多的“打工故事”。在基建热潮还未掀起的时候,最先一波出去赚钱的,往往是刚生育完的年轻妇女,她们去当奶妈,用自己的乳汁,喂养起整个家庭。时间往后推移,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芜湖曾掀起一波“保姆热”,无数的年轻女孩来到北京,成为家庭佣人。《珠穆朗玛》就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曾经的芜湖小保姆的故事:“那些年去北京当保姆的芜城女孩,留在北京嫁人的也有,转行做起小生意的也有,像她这样回来的更多。她们没有学历,没有特长,到哪儿都是做差不多的活儿,像陈荷叶那样真正改变命运的,是极少数。”到了水笑莹的这一代,女孩们的外出更多的变成了求学、工作。《洄游》《鸟居》《世纪大道的夜樱》等故事里,她们是私人家教、教辅机构的老师、大学里的编外人员……
从奶妈到保姆,再到私人教师,女孩们的境况看似在改善、提高,但她们都面临着相同的抉择。妈妈的故事,也会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困惑,也曾是妈妈的困惑。然而,当母亲老去,她们的生活又冒出新的难题:感情、疾病、衰老、养育后代……《百年好合》《去迪士尼》《珠穆朗玛》等篇目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代女性在小说中跨越时空的对望与相遇。也许,在相似的抉择中,我们和母亲之间,能够涌现更多的理解与关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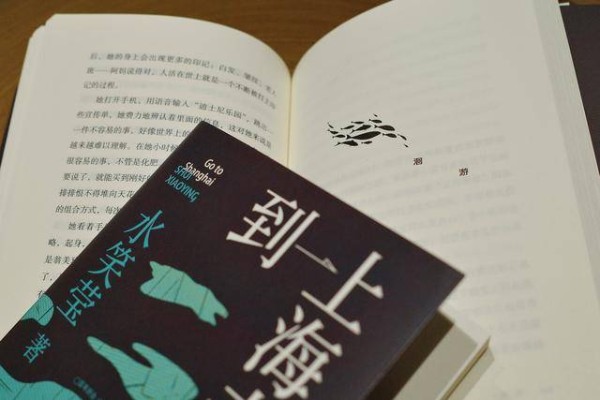
●青年写作者的一种面貌
近年来,文坛涌现了许多的“创意写作面孔”,同样毕业于创意写作专业水笑莹亦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位。
水笑莹,1992年生,安徽无为人,小说创作者,作品见于《十月》《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刊,曾获得第七届“青春文学奖”中短篇小说奖,第一届《青春之歌》文学奖学金,首届“京师-牛津‘完美世界’青年文学之星”提名奖。
相较于异质化、地域化或学院派的写作,水笑莹在《到上海去》中呈现的面貌是朴素的,也是普适的。
她将目光更多地放在普通人的生活,放在平凡的日常中,正如项静在序言《附近的生活与当下的世情》中所说:“她更注意形塑的是附近的生活,在家庭、职场、社区和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真实关系。”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阅读中,总能收获深深的共鸣:
“她并没有为买到烂草莓而难过,让她难过的是整个生活,是出租屋里狭小的厨房、角落生了水锈的卫生间、被冰箱占据的过道所组成的生活。”
“进食变成了一种为了维持生命所必须进行的流程,混合着发票、报价单等,一起成为这个城市运作的流程,妈妈的关心似乎也是某种亲情流程。”
“延迟回家,也是在延迟承认自己的失败。”
“人活在世上就是一个不断被打上印记的过程。”
“人总是想往更远的地方去,但是鱼不一样,没人知道它们为什么要遵循那样的传统,一遍遍回到出生地。”
“锅子像一个欲望的开关,一旦启动,围绕着它的世界便需要作出改变,沸汤一样的欲望潽出来,吓得她赶紧盖上锅盖——她目前显然无法为这些改变买单。”
“她抬起头,看到地铁口那几株吉野樱,夜晚在射灯的照耀下,樱花流露出一种被精心展示的美。她把手机凑上去,有意地往下调,将街道和建筑隔离出画面,只剩樱花在夜空中绽放的姿态,她觉得或许人生和樱花一样,是不需要背景、不需要被解读的存在,只管自顾自地绽放,那就太好了。”
……
这些诚恳、踏实的文字,呈现的是一种不媚俗、不浮躁的青年写作面貌,而这也是《到上海去》值得我们欣喜的部分。
网址:《到上海去》:是小镇女孩的成长史,也是两代女性隔着时间的对望与拥抱 https://www.alqsh.com/news/view/203140
相关内容
小镇道明寺,被心爱的女孩拒绝啦两代茅奖作家乔叶、李佩甫共话“女性的自我觉醒与成长”
刘海粟与两代上海美专绘画作品展揭幕 勾勒百年海派美术传承脉络
对望,是人类不含情欲的心灵之吻 cp 雁回时
小谢含泪接过陌生女孩送来的鲜花 是温暖也是鼓励
上海佛罗伦萨小镇周年庆华丽来袭
出差去上海,也是让我偶遇明星咯
白鲸与萌娃隔着玻璃互动,孩子去哪它去哪可爱至极
相亲的时候中间隔着个媒人,女孩想打哈欠被男孩发现后紧急撤回!
上海佛罗伦萨小镇十周年庆典:一城繁花,十年锦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