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姗姗:超越女性意识的悖论式书写——读施施然诗集《隐身飞行》
《穿越时空的少女》探讨了时间和爱情的奇妙悖论。 #生活乐趣# #日常生活趣事# #读书分享乐趣# #电影推荐趣谈#

超越女性意识的悖论式书写
——读施施然诗集《隐身飞行》
贺姗姗
(原载《北海日报》2025年8月30日6版)
一直以来,我们对施施然的诗歌都有一个标签化的认知和评价,一说到施施然,我们很自然就会说,她是一个美女诗人;一说到她的诗歌,我们就会说,这是典型的女性诗歌,有很强的女性意识。对于施施然诗歌的评价,这些所谓的女性经验、女性书写、女性意识也占了很大的分量。我觉得这不仅是施施然诗歌所面临的一种境遇,几乎所有女性写作者都会经历这样一种困境,像翟永明、王安忆、海男,有关她们最开始的写作也被认定是“女性书写”。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她们”确实是女性的,因为就作为女性写作者而言,女性的诗歌中不可能不带有女性意识,和女性特有的经验和气质,但是我们很少会说某个男性作家或诗人他们的写作是“男性”的,我们在介绍某个男性作家的时候也不会特别加上一个男性的定语,说这是一位“男诗人”。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要高扬女性主义或者女权主义,我只是在提醒当我们在关注一位女性诗人的时候,是不是会因为过于关注“女性”两个字而忽略了她“女性”以外的东西,比如说,她还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跟男性一样写作的“人”。
所以,“女性”两个字对于所有女性作家或诗人来说即是一种优势,也是劣势。优势是人们会因为她的女性身份而给予她更多关注,劣势是从此的她写作会长期被带引号的“女性”所遮蔽,然后不断被标签化、符号化,甚至所有的作品都很难逃离被“女性”化阐释的命运。而在我看来,这种劣势往往都是大于它的优势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文学史中有不少女性写作者,她们的写作一生都被定位在“女性”意义上,并很长时间被笼罩在女性的阐释中。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一方面,评论家们在不断强化她们的“女性意识”,为她们造就了一种藩篱,一种窠臼;另一方面她们自己可能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写作认知,“我的作品就是女性的。”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女性的没有什么不好啊,现在男女平等啊”,但是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女性作家都不想只做一个“女性作家”,尤其对于一个成熟的写作者而言,任何标签化的、符号化的固化阐释都是一种束缚,她们也许更想被认定为一个普通的、不那么“女性”的写作者。当然,这首先需要写作者自身的努力,她需要有意识地把自己放置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和角度来对整体生命、生存现实作出自己的观照和回应。
在《隐身飞行》中我看到了这样的尝试和努力,诗集里的很多诗渗透出一种强烈的超越“女性意识”的书写,比如《宿命》《悖论》《戒律》《惯性》《沙棘》等,它们更着力于去表达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思考和对人类整体生存现状及生命意识的哲学思考和观照。其中我最喜欢《悖论》这首诗,它让我想到了英美新批评家布鲁克斯在他那篇著名的《精致的瓮》中所提到的“悖论”诗学,他认为:“诗的语言就是悖论的语言”,悖论这种非逻辑甚至反逻辑的语言就是表达真理的语言,而诗人想要表达真理,必须使用悖论。他甚至强调“无诗不悖论,无悖论则非诗。”在我看来,施施然的很多诗中都充斥着这种悖论艺术,也正是这种悖论式书写,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技艺上的自我突破。
单就《悖论》这首诗来看,诗人写到“他们惯常用一种正确反对/另一种正确。用这个自由/反驳那个自由/当你试图注视/他们面目模糊如同你正看向深渊/我为我永远也无法理解你正看向深渊/我为我永远也无法理解一些事物/感受到活着的耻辱/而这正成为我们越来越庞大的日常”,它颠覆了诗人以往给我们的留下唯美的、浪漫的、诗意书写,而带来一种新的质地和杀伤力,在她看似平淡、冷静、理性、克制的叙述中,实则隐藏着一种格外犀利、敏锐、坚硬、深刻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比猛烈本身更有爆破力,它增加了词语本身的重量,使语言充满张力,处处表现的理性的力量,在矛盾的对立中给人的思想和灵魂带来一种清醒的撞击式,从而在四两拨千斤的艺术效果中达到了对生活表象的去蔽和对生存真相的揭示。
不仅仅是这一首诗,《宿命》中也有这样的悖论性书写:“我需要回归,所以/我不停地出走/我需要圆满,所以我/不停地打碎自己/我需要建立因此/我破坏,破坏!”诗人在回归-出走、圆满-打碎、破坏-建立中的二元对立中,不断对自我进行解构和重构,从而实现了对自我的深刻观照,完成了对生存真相的揭示——出走意味着回归,打碎中意味着圆满,破坏则意味着建立。在《戒律》一诗中,一群僧侣和一个女人相遇,并用目光“相互刺探”,僧侣和女人各有戒律,然而吊轨的是,这种戒律中恰恰隐含着对戒律的突破,这未尝不是一种深刻的悖论。在《风与爱情》中,爱情像风一般充满了悖论,“我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吹到的风/都是同一场风”,“我们这一生/爱国很多人/其实都是同一场爱情”,这里诗人再次揭示了爱情的本质,有形或无形,永恒或消失。在《死并不意味着消失》中,“死去的人,看见厄运/落在幸存者身上”,这是生与死的悖论,死亡意味着更广阔的生,而生意味着另一种死。还有《镜中》的我与你,“拥抱”即“囚禁”,而“我终会失去你”也就意味着“你失去我”。施施然尤其擅长写“物”,她常常在对日常事物的观照中发现抒发哲思,比如在《鸢尾》中,她看到一株坠落在泥土中的鸢尾仍旧在飞翔,这是自由的化身,因此它“落在地上也是飞翔的样子”,被折断了翅膀的“自由”亦能飞翔。再比如《沙棘》中:“为了包裹甜,它分泌酸/为了困住爱,它长出嚣张的刺”。这种悖论式的语言不仅存在于对生命的观照,对物的书写,还体现在她的一些游记思考中,比如在《想和你在爱琴海看日落》中“你是现实。也是虚拟/海面上空翻滚的云,生命中曾压抑的激情”,“相爱,相恨/再灰飞烟灭,原谅我,一遍爱你/一遍放弃你”这是爱与恨的悖论;在《四月,独自在布达佩斯醒来》中“我们获取,又失去/我们走近,又远离”这是得到与失去的悖论……
对于诗人而言,悖论不仅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艺术,更是一种思想和语言的交锋和历险,在这种交锋中,他们一次次承受矛盾的纠葛的对立的疼痛,从而抵达一种生命的真实。海德格尔曾说“真理必须搏而后得”,它需要经历一场语言暴力的搏斗后才能获得,而悖论和反讽在某种程度上则赋予了这种暴力,这使得诗人的书写不再轻快,而多了一份沉重。就像她自己的诗句:“我喜欢写诗,让针刺进日渐崩塌的心灵。”正是这种像针刺一般的语言暴力和悖论书写,使施施然看似理性、克制的语言中蕴藏着一种颠覆式的力量,从而超越了“女性书写”的窠臼和藩篱,为读者带来一份沉甸甸的诗意思考。她的诗歌告诉我们,悖论未必需要故作惊奇,平凡的事物、平淡的笔调亦可带来不凡的张力效果,日常语言的暴力或许更有冲击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施施然的在时空幻境中的“隐身飞行”,实则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观照,而作者的“隐身”让词语和真理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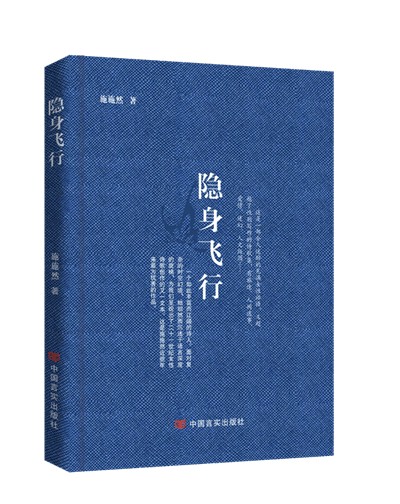
《隐身飞行》,施施然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贺姗姗,河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在读博士,评论散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星星》《诗选刊》《河北日报》等。
网址:贺姗姗:超越女性意识的悖论式书写——读施施然诗集《隐身飞行》 https://www.alqsh.com/news/view/225411
相关内容
施施然诗集《隐身飞行》分享朗诵会在石家庄举行施施然诗集《隐身飞行》推荐语 | 邱华栋、海男、杨庆祥、戴潍娜
专访 | 诗人施施然:作诗之人,光有个性和才气也没用
施施然:“中国诗歌走向欧洲”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贺峻霖施下的蛊,唯一中招的是严浩翔
梁洛施和郭嘉文,两位女性,一段情感纠葛……
撕掉之前的标签,“外卖诗人”王计兵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出版
“施坦威SPIRIOCAST”亚太区发布 暨施坦威中国二十周年庆典音乐会在京举行
这就是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找回的女孩……施柏宇 陈昊宇 施柏宇
施佬:台湾的“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