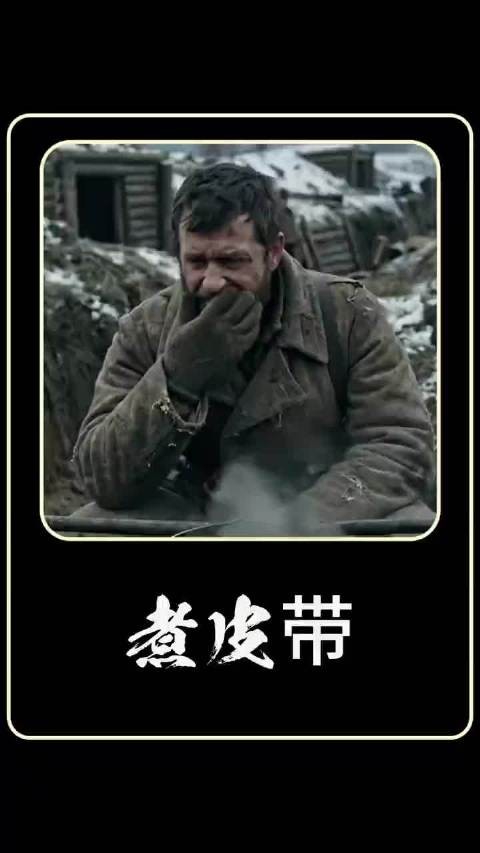技艺与权力的辩证:当代杂技美学的现代性困境与突围
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生活艺术强调古典美学与当代审美的结合 #生活乐趣# #生活艺术# #生活美学设计# #传统与现代融合的生活艺术#
张学标

《扬帆追梦·浪船》演出海报
在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南充分会场活动的璀璨舞台上,当《扬帆追梦·浪船》的演员们在精心设计的“浪船”道具上完成一个个高难度动作时,这个由武汉杂技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创演的杂技节目,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杂技艺术发展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样本。节目通过“四人连翻”“单人180度飞跃跨桥”“团身三周自落桥”等不断突破人体极限的高难度动作序列,不仅展现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精神内核,更折射出中国表演艺术在全球化语境中面临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个体与集体等多重张力与矛盾。演员们在声光电巧妙构筑的虚拟风浪中精准完成“六人连翻”等高难动作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艺层面的突破,更是一种文化表征的复杂运作机制。这个将源于唐宋时期的古老浪桥技艺与现代舞台科技进行创造性融合的节目,自2021年首演以来先后获得文华奖提名、中国杂技金菊奖、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银小丑奖”等重要荣誉,其艺术实践恰如一面多棱镜,清晰映射出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遭遇的诸多深层悖论

武汉杂技团《扬帆追梦·浪船》节目作为德国纽伦堡FLIC FLAC圣诞马戏压轴节目闪亮登场
杂技艺术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身体规训与艺术自主性之间持续博弈的复杂辩证。在《扬帆追梦·浪船》这个具体案例中,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认证的“浪船”道具系统,通过精心设计的隐藏式栈桥和精密启升装置,实现了表演空间的革命性拓展。这种技术创新在提升观赏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演员身体纳入更为严密的技术控制网络之中。年轻演员张艺琼在德国赛前训练时头部磕伤仍坚持演出的真实事例,在感人的励志叙事背后,深刻暴露了当代艺术生产体系中隐含的身体治理逻辑;而主演鲁国祥在18岁生日当天于蒙特卡洛经历获奖体验的个人故事,则生动折射出国际艺术评价体系与个体成长轨迹之间的复杂交织。当“高难度”日益成为核心评价标准,当技术创新被简单等同于艺术进步时,杂技艺术的本体价值正在面临被技术理性所异化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不仅体现在身体与技术的失衡关系上,更深刻地反映在艺术评价体系和文化认同建构的多个层面。
一、创新迷思:技术崇拜下的艺术本体危机
《扬帆追梦·浪船》最引人注目的创新体现在其技术架构的全面系统性升级。从道具系统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认证,到声光电技术的沉浸式创新运用,再到多人协同高难度动作的突破性设计,这些要素共同构建了一场令人眩目的技术奇观。这种创新模式深刻呼应着当代表演艺术领域普遍存在的趋势:科技要素日益成为艺术价值的核心评判标准。然而,当武汉杂技团在各类宣传资料中反复强调“全球独一份”的技术独创性时,杂技艺术的身体本质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传统浪桥技艺的独特魅力本在于个体身体的极限探索与即兴发挥,而《扬帆追梦·浪船》通过系统性技术重构将其转化为高度程式化的集体性空间叙事。这种转变的深层代价是身体主体性的消解——演员不自觉地沦为技术装置中的标准化构件,其身体技艺必须严格服从于整体视觉效果的工业化生产需求。
更具批判性的是,当创新过度聚焦于技术突破时,杂技艺术与生俱来的民间性与即兴性特质正在加速流失。武汉杂技团道具研发部负责人胡彬展示的国家知识产权局签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虽然从法律层面证明了技术创新的独特性,却无法必然带来艺术价值的实质提升。这种明显技术导向的创新路径,暴露出当代艺术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创新焦虑”——将技术创新简单等同于艺术进步,将专利数量机械对应创作质量。正如该节目历经六七次道具升级才最终定型的漫长过程所示,这种思维定式可能导致杂技艺术在追求“新奇特”的过程中,丧失对其本质特征的坚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浪桥表演中那种因偶然性而产生的独特美感,在高度技术化的《扬帆追梦·浪船》中已难觅踪迹,这不禁令人深思技术理性对艺术本真的侵蚀程度。武汉杂技团创研部主任华乐提及的“演员们腿上几乎一直没有好过”的训练状况,既体现了专业训练的严格要求,也从侧面反映出技术创新背后身体付出的沉重代价。

《扬帆追梦·浪船》演出片段
从艺术哲学的角度看,这种技术崇拜可能导致杂技艺术陷入“创新悖论”:越是追求技术创新,反而越可能远离艺术本质。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论述,在这里具有新的现实意义。当杂技表演可以被精确复制和技术量化时,其“灵韵”(aura)正在逐渐消失。此外,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技术奇观背后的真实性问题。当浪船表演越来越依赖技术装置时,演员的真实身体体验与观众的艺术感受之间是否出现了新的隔阂?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美学问题。具体到《扬帆追梦·浪船》的创作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创新与艺术本质之间存在的深刻张力:一方面,获得国家专利的浪船道具系统通过隐藏式栈桥和启升装置,实现了从传统的一桥一人表演到一桥多人表演的革命性突破,创造了“六人连翻”等前所未有的高难度动作;但另一方面,这种技术突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当表演越来越依赖精密的技术装置时,演员的身体表达是否受到了新的限制?当表演的每个环节都被预先精确设计时,即兴发挥的艺术魅力又如何得以保留?
二、国际奖项背后的文化政治博弈
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银小丑奖”的获得,使《扬帆追梦·浪船》正式进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杂技艺术评价体系。摩纳哥公主斯蒂芬妮亲自颁奖的仪式性场景,构成了一幅充满后殖民色彩的文化图景。这种看似中立的艺术认可,实则潜藏着深层的文化权力关系。武汉杂技团派出以年轻演员为主的19人团队参加第46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其中15名演员是首次参加国际大赛,这种特殊经历既是对外交流的宝贵机会,也可能在无形中强化了对西方艺术评价标准的依赖。该节目在德国、摩纳哥等国的巡演,虽然拓展了文化影响力,但“文化输出”的单向度逻辑依然难以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审美霸权。特别值得反思的是,当这些年轻演员在得知获得“银小丑奖”时流下的泪水,既包含着成功的喜悦,也可能隐含着对西方艺术标准的内化认同。

《扬帆追梦·浪船》亮相第46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
从后殖民理论视角看,这种国际艺术交流中存在着微妙的文化权力关系。赛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批判在这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西方观众和评委对东方艺术的期待往往带有某种“他者化”的凝视。霍米·巴巴的“杂交性”理论则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交流中产生的新的可能性。中国杂技艺术在国际化过程中,需要警惕单纯满足西方对“东方奇观”的想象,而应该致力于建立真正的跨文化对话。这种对话不是简单的文化输出,而是通过艺术语言的创新,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度理解。具体到《扬帆追梦·浪船》的国际巡演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对话的复杂性:当节目在摩纳哥、德国等国家演出时,其受到的欢迎既体现了中国杂技艺术的国际认可,也反映出国际艺术市场对中国文化的特定期待。这种期待往往夹杂着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想象和对“中国特色”的刻板印象,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国际艺术场域中保持文化主体性,是中国杂技艺术国际化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特别值得深入反思的是节目对“乘风破浪”意象的刻意强调。这个被官方阐释为“武汉精神”的隐喻,在国际传播场域中极易被简化为单一的国家叙事注脚。当技术创新与民族认同过度捆绑,艺术表达的自由空间就会受到无形挤压。武汉杂技团在海外宣传中突出强调的“中国独创”技术特征,这种表述本身就可能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真正的跨文化对话应建立在平等互鉴的基础上,而非简单的符号竞争。需要清醒认识到,在国际杂技艺术的交流中,我们往往过度注重奖项的获取,而忽视了更深层次的艺术对话和美学思想的碰撞。正如教练华乐所言“演员们还年轻,他们更应该在艺术道路上超越以前的自己”,这句话或许暗示着对当前过度追求国际认可现象的一种隐性批判。这种批判意识在副团长陈健为鲁国祥煮生日面的温馨场景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那个夜晚演员们既品尝了成功的喜悦,也体会了艺术国际化的复杂滋味。
三、身体规训与艺术表达的张力
《扬帆追梦·浪船》长达四年的系统训练历程,清晰地展现了一套严密的艺术生产机制。从主演鲁国祥苦练“团身三周自落桥”的艰辛历程,到00后演员们带伤坚持训练的身体记忆,这些叙事在展现专业精神的同时,也暴露出艺术生产体系中的身体治理术。法国思想家福柯所揭示的规训权力在这里得到生动体现:训练场地的空间布局、每日重复的技术操练、集体动作的精准要求,共同构建着演员的身体惯习。武汉杂技团创研部主任华乐提到“演员们腿上几乎一直没有好过”的训练状况,既体现了专业训练的严格要求,也折射出艺术生产体系中对身体极限的挑战边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岁女演员张艺琼在德国训练时从高空摔下磕破头部,却依然坚持用头发遮掩伤口完成演出的事例,既展现了职业精神,也引发了对身体代价的深刻思考。
从身体哲学的角度看,这种训练体系体现了现代性对身体的深刻规训。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演员身体经验的独特性。在杂技训练中,身体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主体与世界交互的媒介。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关于“文明进程”中身体规训的论述,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杂技训练中的身体管理。此外,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论”为分析舞台上下身体的不同表现提供了理论视角。具体到《扬帆追梦·浪船》的训练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演员身体经历的双重规训:一方面是通过重复性训练形成的技术规训,使身体能够自动完成高难度动作;另一方面是通过艺术规范形成的审美规训,使身体表演符合特定的美学标准。这种双重规训虽然保证了表演的专业水准,但也可能抑制身体的自然表达。例如,演员需要在不间断的摆动浪桥上完成精确的翻腾动作,这种训练要求身体达到极度的标准化和可控性,但也可能削弱了表演中的即兴发挥和个性表达。
然而身体从来不是完全被动的存在。18岁的鲁国祥在生日当天带着“金小丑”的梦想登台,在未能获得金奖后说出“不经历过失败的苦涩,哪能体会到成功的滋味”的感悟,这些细微的身体实践蕴含着对艺术自主性的深切渴求。年轻女演员张艺琼在头部受伤后仍坚持演出,用头发遮掩伤口登台的专业选择,体现了演员对艺术表达的执着追求。这些鲜活案例提示我们:真正的艺术创新应该源于身体的创造性表达,而非对技术标准的机械遵从。当前杂技教育需要打破过度技术化的训练模式,在规训与解放之间找到动态平衡。正如该节目从最初带着保险绳训练到最终自如表演的演进过程所展示的,艺术精进的本质在于实现技术规范与个性表达的辩证统一。武汉杂技团第四代至第八代演员共同参与创作的特殊背景,更使得这种身体传承具有了跨代际的文化意义,体现出技艺传承中的身体记忆与创新精神。这种代际传承不仅体现在技艺的传授上,更体现在艺术理念和身体经验的传递中,老一代演员的经验与年轻演员的创新意识在训练和表演过程中不断对话、融合,形成了一种动态的传承机制。
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路径探索
《扬帆追梦·浪船》对传统浪桥技艺的革新,提出了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经典命题。节目将历史悠久的浪桥技艺,通过系统性创新和叙事重构,赋予了鲜明的当代审美特征。武汉杂技团从2017年开始构思,经过多次“头脑风暴”和六七次道具升级,最终打造出具有隐藏式栈桥和启升系统的浪船道具。这种转化确实拓展了传统技艺的表现空间,但其中隐含的“创新焦虑”也值得警惕:当“新”成为绝对价值时,传统的精髓可能在这种追逐中被稀释。道具研发负责人胡彬强调的“锦上添花易,从无到有难”的创新历程,既体现了创作团队的执着,也反映出传统技艺现代转型的艰难。
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角度看,杂技艺术的传承涉及身体化的文化记忆。德国学者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指出,身体是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在杂技训练中,技艺通过身体化的实践得以传承,这种身体记忆比文字记录更能保持传统的生命力。同时,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杂技技艺传承中的身体化过程。传统浪桥技艺中蕴含的不仅是技术动作,更是一整套身体感知和运动方式,这些都是需要在新语境中创造性转化的宝贵资源。具体到《扬帆追梦·浪船》的创作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多个层面:在技术层面,通过道具创新拓展了表演的可能性;在叙事层面,通过“乘风破浪”的意象赋予传统技艺新的象征意义;在传播层面,通过国际巡演和参赛使传统艺术进入当代全球文化交流场域。这种多层次的转化既体现了对传统的尊重,也展现了面向未来的创新意识。
该节目对“城市精神”的意象化表达,代表了当下传统文化创新的普遍模式:将地方性元素与主流叙事结合,打造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化产品。但这种创新模式是否过于程式化?当“乘风破浪”的隐喻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文化产品时,艺术表达的独特性正在被象征符号的标准化所消解。真正的创造性转化应该是对传统文化内核的深度激活,而非表象化的符号拼贴。武汉杂技团计划将“浪船”技艺融入2024年新剧目的尝试,或许预示着一条更可持续的创新路径——让技术创新服务于艺术表达的本质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浪桥技艺中蕴含的民间智慧和身体记忆,需要通过创造性转化才能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这要求创作者在创新过程中保持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敬畏之心。鲁国祥所说的“每一代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跟我的老师们、队友们合作出更好、更厉害的技巧”,这句话或许暗示着传统技艺传承中代际创新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这种代际对话不仅体现在技术传承上,更体现在对艺术本质理解的深化上,年轻演员的新视角与老一辈演员的丰富经验相结合,可能开辟出传统艺术现代表达的新路径。
结语:在技艺与人文之间寻找杂技艺术的当代性
《扬帆追梦·浪船》在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中的精彩呈现,生动映射出中国当代杂技艺术发展的复杂图景。这个杂技节目从2017年开始构思,历经四年精心打磨,最终在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获得“银小丑奖”的艺术旅程,见证了中国杂技艺术在国际化道路上的探索与突破。当演员鲁国祥和他的队友们在颁奖典礼后分享生日的喜悦与遗憾时,当年轻演员们带着伤痛依然完美完成每个高难度动作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杂技节目的成功,更是整个中国杂技艺术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缩影。这些年轻演员在蒙特卡洛流下的泪水,既为获奖而流,也为四年来在武汉杂技厅度过的无数个训练日夜而流,这些身体记忆已经成为节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更宏观的文化研究视角来看,杂技艺术的现代转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普遍挑战。如何在全球与本土、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市场之间找到平衡点,是所有传统艺术形式都需要面对的问题。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关于“编码-解码”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杂技表演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接受差异。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深描”理论则提醒我们关注杂技艺术背后的文化意义网络。具体到《扬帆追梦·浪船》的艺术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杂技艺术在当代发展的多重可能性: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和艺术创新,传统技艺得以在现代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通过国际交流和文化对话,中国杂技艺术正在探索具有全球意义的艺术语言。这种探索既需要技术上的突破,更需要文化理念上的创新,需要在保持文化特质的同时,开拓具有普遍人类意义的艺术表达。
杂技艺术的未来发展,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持续创新,更是对艺术本质的深刻反思。武汉杂技团创研部主任华乐指出“演员们还年轻,他们更应该在艺术道路上超越以前的自己,也许这才是比赛的意义”,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艺术创新的真谛。真正的突破应该体现在艺术本体的深化和表达方式的革新上,而非仅仅停留在技术难度的提升。当《扬帆追梦·浪船》的演员们在浪潮造型的道具间翻飞时,我们期待看到的不仅是视觉奇观,更是身体艺术的本质力量——那种源于生命本能的表现力,那种超越技术规训的艺术自主性。从“金菊奖”到“银小丑奖”的获奖历程,既是对节目艺术质量的肯定,也预示着中国杂技艺术国际化进程的新阶段。这个过程不仅关乎一个节目的成功,更关乎中国表演艺术整体发展的方向选择,需要在艺术性与观赏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中国杂技艺术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在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保持必要张力,在集体表达与个体创造性之间寻求和谐共存。正如“浪船”的意象所喻示的,这条艺术发展之路需要在风浪中不断调整航向,在追梦的过程中保持对艺术本质的坚守。武汉杂技团计划通过新剧目继续深化“浪船”技艺的探索,这表明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非终点。唯有如此,杂技艺术才能在现代艺术生态中真正实现其美学的当代价值,才能在全球化语境中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这不仅关乎一个艺术形式的生存与发展,更关乎如何在现代性条件下重新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既保持文化自信,又具备批判意识,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使杂技艺术真正成为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这种探索不仅具有艺术本体的意义,更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张学标,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
网址:技艺与权力的辩证:当代杂技美学的现代性困境与突围 https://www.alqsh.com/news/view/237275
相关内容
铁幕下的微光:第二十回中的人性突围与权力博弈潮剧评|浙产剧《藏海传》:东方美学与当代叙事的双重变奏
观后感:破局者的勇气——重审《司马光砸缸》的现代性突围
龙族:路明非的时代孤独:当代青年的镜像与精神困境的文学投射
二战德国军服:权力美学的巅峰之作
杂技舞剧《化·蝶》在广州火热上演
杂技艺术从创新中走向未来
“中国杂技之乡”缘何闪耀世界
进入“剧”时代,杂技向何处行
海派杂技与维吾尔族非遗同台亮相 再现动人沪疆情